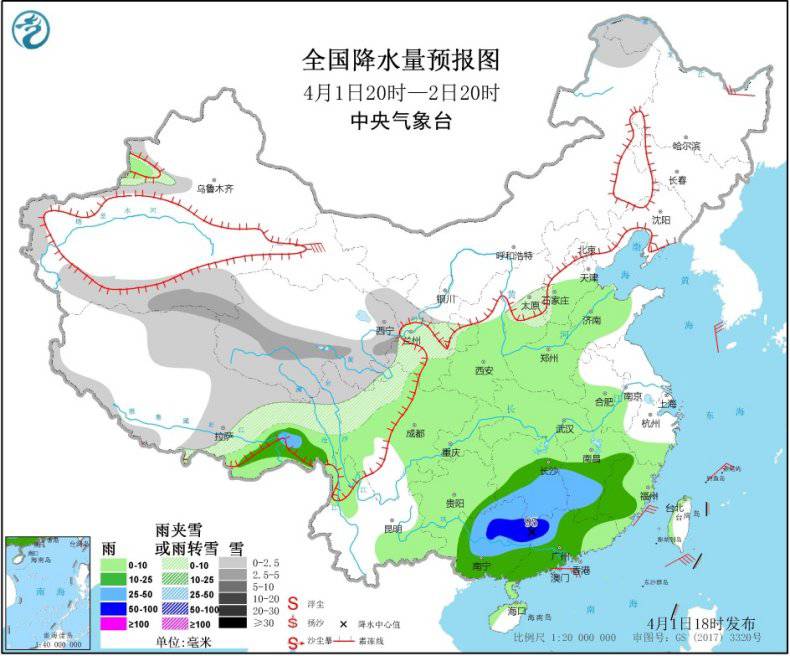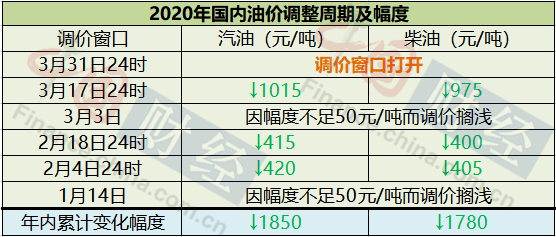尚珩在河北长城调查时测量墙体尺寸
雄伟壮丽的万里长城在古代除御敌之用,在当时、近现代社会还有防疫的功能。日前记者采访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工作的长城专家尚珩时,他几次强调了长城的防疫功能。
尚珩还有另一个身份——长城小站站长。长城小站成立于1999年,一直致力于长城保护和知识普及,尚珩去年接了站长之职。国家文物局很重视小站的工作,2016年发布的《中国长城保护报告》“社会力量参与长城保护”章节中点名写到长城小站,长城小站的公众号里更是可以看到一系列的荣誉奖项。
尚珩出身考古专业,受家学影响,从小就对文史深感兴趣。浸淫于长城文化的十几年,从专业出发的他对长城有了更加冷静和深入的感悟和思考。
疫情
对沿线经济的损害要远大于踩踏
我们都熟知长城的御敌功能,而历史上其在防疫方面也曾起到不小作用。
一道长城,首先可以起到阻隔之用。尚珩举例,陕北地区曾经狼患泛滥成灾,威胁内地,而长城像是面对草原的一道屏障,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草原狼的进犯。
另外,民国时曾经暴发鼠疫。民国政府为了防止鼠疫蔓延,采取控制人员流动的方式,在长城便设置有关卡,对南来北往的人进行检测。山西在这方面所做最为突出,充分利用了其域内的长城优势。
长城在防止自然灾害方面作用也不小,比如对大风、洪水,都能起到一定程度的阻隔作用。
此次新冠疫情期间,长城景区也暂作封闭,游人减少,人为踩踏有所减轻,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长城?尚珩说,虽然长城免遭了踩踏,但疫情对长城沿线经济的损害要远大于此。比如怀柔区的农家院基本靠长城旅游生存,疫情期间,村庄封闭管理,游客、实习的学生无法前往旅游、实习,客流量的稀少对经济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。
“长城这个地方属于捧着金饭碗要钱。”尚珩慨叹,今后如何理解保护和利用,使两者结合得更好,始终是一个重要课题。
行走
最悬的一次,是冬天走祖山
尚珩1984年生人,父亲以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,虽然做行政工作较多,但对他影响颇深。尚珩笑说,很多人在高考时会有迷茫,不知道要学什么专业,我特别明确,就是要学考古。
尚珩期望用实物去和古人对话,觉得那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。在读明代戍边名将戚继光撰写的书中,他想到了金山岭长城,“那是戚继光的一个实验场,在戚继光写的书里所看到的内容,在金山岭几乎都可以看到实物,而这些东西到其他地方是很难看见的。比如戚继光要求守卫垛口的士兵要把名字写在垛口边的墙壁上,现在我们在金山岭就可以看到当时写名字的地方。”
考古专业当年属于冷门,报名人少,录取分数低,“不但好考,还好就业”。尚珩本科班42人,有22位到考古工地实习,毕业后便去各地的考古所工作。考研,也好考,冷门,分数低,人数少,毕业后顺利到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就职。
从1991年第一次上长城八达岭之后,尚珩顺势走了司马台、居庸关、黄花城、黄草梁等处长城。1999年,走古北口,那一次给尚珩留下了深刻印象,因为那是他第一次行走穿越线。“从古北口走到金山岭,再走到司马台,那一次走了三天。”第一次走野长城,而且是连续穿越,长城的绵延悠长由此增加了他的感性认识,对他之后的路影响至深。
2001年去过黄草梁后,尚珩发现了长城小站。
“从黄草梁回来,写了一篇游记,就想要不要在网上发一下,一搜就搜到了长城小站,一看挺喜欢就点进去了,里边有一个长城论坛,在那里发了这次旅行的游记。现在那个论坛还在,保持1999年的初创风格,特别low。”之后,尚珩就和小站的朋友走到了一起,常常参加他们的线下活动。
2003年后,尚珩开始系统走长城,背起大包,装上帐篷、睡袋,“负重大概一般在五六十斤,而且因为走的人少,路都不是很好走,所以都比较辛苦”。尚珩回想,当时交通不便,也没有攻略可参考,所以尚珩和朋友们出去一般需要包车,利用五一、十一长假。“坐车到一个点,然后背着包走。一般扎营两个晚上,第三天中午下山,去村里补给一下。”这样一点一点走下来,到2006年,从河北东部到北京平谷这一带的长城,尚珩和朋友们已经基本走过一遍。
2004年走祖山,是尚珩和小站朋友走得最悬的一次,也是他第一次冬天走长城长线。那是一个林场,现在是一个景区。
尚珩印象中,祖山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,植被特别好。“当时我一直认为那个地方是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,日本人在长城沿线修的千里无人区的一小块残留。”
尚珩和两个朋友利用春节长假,年三十晚上到达秦皇岛,初一一早上山。“特别冷,而且白天时间短,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,每天走不了多少就得扎营。”按照以往经验,第二天午后都能找到补给处,但在祖山找不到。到第三天,水都没有了。“虽然冬天耗水少,但没水也不行啊!”尚珩们想办法,找阴坡处的积雪,“这是冬天的好处”。他们把积雪表层的脏雪拨掉,捧里边稍干净一点的拿来化掉喝下去。但实际上尚珩他们都知道这样不好,因为雪的泥含量比较高。
又忍一晚,第二天一早他们判断方向,沿山谷向河北也就是长城内侧走,“因为那里肯定有人”。在接近山顶处发现一处泉眼,沿着泉眼向山下又走5个多小时,终于见到一户人家,“那个人自己包了一片山,在那儿种核桃”。略歇歇脚,再走。3个多小时后,出山见公路,已是下午了。
变化
照片、网文成了盗贼指路牌
近几年,尚珩明显感觉到了长城沿路的变化。“祖山修了路,走势好极了,简直成了阳光大道,基本上就是我们当年走的那条。”
现在去长城是方便,以前是神秘感。“现在每天走多少,大概能看见什么,心里基本清楚,以前完全不知道,也没有攻略和资料可以查。即便资料上有,也是文字,带不来感性认识。”当时尚珩和小站朋友会向碰到的放羊人询问当地情况,现在不用,攻略比老乡们讲得还清楚。
以前的长城上因少有人迹,几乎见不到垃圾和刻字。“现在我们看见石头上有刻字都会骂刻字的人,但我们当时看见会觉得终于看到了人啊!看见垃圾也一样,哪怕是一个烟头,都会有特别高兴的感觉。”尚珩在走河北东部长城时,在一个烽火台中看到“长城四怪”的刻字,背包走得正累,猛然看到这么个刻字,亲切感油然而生。“当然现在完全不一样了。”尚珩说。
另外一个明显变化,是文物丢得多了,尚珩认为一部分原因是爱好者处置不当惹的祸。
长城上有不少明代遗留文物,像带字的砖、石碑,河北东部、北京深山区都有。“但很多地方10年前去看到的,再去没有了。比如祖山,2004年去时,基本每座敌楼都有一块石碑,碑上刻着修建时间、修建人、碑的尺寸,现在很多都失踪了。”
“还有古北口,有人为了偷一块好砖,把周围的砖凿掉,这样就在墙上弄出好多坑。而这些人有了好砖还不满足,他把那些品相不太好的砖也凿毁。”尚珩说,类似于这种事挺多,河北东部比较严重。
还有一个重要特点,以前的人消息闭塞,而今大家去玩都拍照片,也喜欢发到网上。尚珩的一个朋友就是这样。他在某处看到了一块北朝时期的石刻,发现没人管,周围布满垃圾,于是拍了照片,回来发到公众号上,一年后,他再去看这块石刻,发现已经没有了。
尚珩认为公众号上的那篇文章就是给盗贼的一个指路牌。“人家都不用踩点,通过你的照片就能知道东西好不好,还有具体地址。”这样的事不限于长城,在蔚县,尚珩曾看到寺庙里的壁画被偷,都在未被开发而爱好者常去的地方。
后来尚珩感慨,我们出去看到好东西,不要那么明确它的状况,这些未被认证身份的文物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,很容易被偷,智慧一点就是保护它们。
尚珩和小站朋友也做过使文物得以安身的事。在密云五座楼下的农家院中,他们发现一块长城碑,农家院已倒闭,石碑被扔置院中。通过和当地文物部门的沟通,尚珩和朋友们把碑送进了博物馆。
尚珩认为,在长城旅游时可以顺手做很多事,不只是捡垃圾,也可以做文保。比如一个文物没有纳入文物管理体系,或者没有得到文物身份认证,就可以向当地文物主管部门申请,把它增加为文物点。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,尚珩为有不少这样的爱好者感到欣慰。
研究
我们看到的长城并不是明代时的样子
2007年启动全国长城资源调查时,尚珩正在山西大学读研究生,他也参加了山西长城的调查工作。当时他跟着队伍调查长城主线以内的烽火台、城堡,大概跑了十几个县、几百座烽火台。这一趟的亲身经历,让尚珩似乎摸到了长城保护的切要所在。
尚珩感到,那次长城资源调查时,调查队员虽然都是当地文物部门或考古所的工作人员,但实际上大部分队员对长城的了解程度并不高。从根本上说长城资源调查本身不是一个学术行为,而是摸家底的管理行为。调查时,只要出现遗漏,它的身份就无法纳入长城保护范围,也就得不到《中国长城保护条例》的保护,若在日后出现问题,文物部门就会很被动。“当年我们调查时就漏掉了一个墩子(烽火台)。2009年当地修高速,这个墩子碍事,施工人员看长城库里没有它,就给拆掉了。”
这使尚珩越发感到保护长城是一件难事,体量大、跨度大、分布广、绝大部分区域经济不发达。“它不像故宫只是一个院子,并且当地老百姓对长城保护没有太多概念,他们就觉得那是个土垄子,有什么值得保护的。”尚珩还提到,现在爬长城的人越来越多,如果保护措施跟不上,就意味着会出现人为破坏。“箭扣长城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。”
在尚珩心中,长城研究也是一件麻烦事。他的观点明确:要保护长城,一定要先懂它。“不懂怎么保护呢?举个例子,长城墙上有洞,那是古代安装窗户框时的卡槽,木头框年代久远没有了,修的人不知道是干吗用的,就把洞用砖给堵上了。”由于基础研究的薄弱,在制订应用研究或应用保护领域保护方案,特别是细化方案时,便容易抹掉本该保留下来的历史信息。
长城修缮成功案例多,失败案例也不少。尚珩又举一例,“有时城墙上从顶到下会有一道缝,那不是墙裂了,那或者是当年修长城时两家施工队的分界线,或者是建筑上预留的伸缩缝,有的修复就把这道缝填上了,历史信息又被抹掉了。”
尚珩做过统计,做长城研究的人,基本属于兼职,而年轻一辈的长城研究者多来源于2007年的长城普查。那一次普查的另一目标即为培养长城人才。“严格地说,这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也达到了,但兼职来做毕竟时间有限,另外人数也太少。大概算一算,全国做长城研究的三四十岁者在50人左右,主要集中在考古圈,历史圈也有但不多,大家基本都认识。”
尚珩总结,从传播效果看,基础研究的不足不仅影响长城的修缮保护,知识普及也受到影响。这个问题目前提及不多,但作为圈中人,会感触较深。2018年,尚珩去做八达岭一个烽火台的保护工作。那处烽火台从现状看是一个土堆,在制订方案时也是按照土长城烽火台去做的,但是尚珩将烽火台挖出来之后,发现是砖式结构。“这说明我们看到的长城并不是明代时的样子,因为它的损毁太严重。有时我们连长城两侧的边界位置都不清楚,因为它塌了。而通过考古发掘,就可以知道古代时它的边界在哪儿,采取了什么工艺,修过几次,是什么结构,这些了解得越明白,越能做好保护工作,做考古发掘就是为今后的保护提供依据。”
教育
长城保护员是基层文物部门的眼和手
长城沿线的教育也是长城小站格外关注的领域,他们认为保护长城的一线人员是沿线村庄的村民。当地孩子更是未来的希望,小站联合长城沿线的学校,举行长城知识大赛、长城作文比赛,普及长城文化。这些活动从2004年启动,十几年过去,很多长城下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吧!至今,长城文化普及已经不局限于长城沿线,北京周边,小站的志愿者们也组织过多次长城知识进课堂活动,仅去年就举行了几十场。文保和教育,是小站长此为之的事。
小站的公众号还提供基础长城服务,比如可以看到长城地图:目前已知的明长城走向,烽火台位置、名称及位置图,还有历史年表检索、长城法律文库,这些主要是针对基层文物部门而做,全部免费。尚珩自己身在基层,了解基层文物部门人少、活多、地位低的现状。“干活都挺不容易的,我们就想把跟长城有关的汇总在一起,这样基层文物部门在需要时,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它们。”尚珩认为只是给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,这些惠人之事,小站的很多志愿者都在做。
长城保护员,小站的长城知识普及也没有忘记他们。保护员的综合素质要提升,方法只有一个,就是做培训。2018年始小站与各地文物部门合作,为长城保护员提供培训。“培训内容很多,包括长城基本知识、法律法规、户外风险和安全等等,延庆今年该做第三期了。”
尚珩说,从反馈来看,长城保护员很希望得到这些知识。而长城保护员对于基层文物部门来说,也是他们的眼睛和手。“基层人员少,本身的专业知识素养也不是很高,实际管理起来是比较费劲的。利用好长城保护员就是给自己长了眼睛和手,把他们培训好了,可以给管理部门提供技术支持。”
转变
被纳入古遗址之后
近几年对长城保护的重视程度提高,有几个明显例子,需要跨长城的基建项目,比如修高速,最初是简单粗暴,把长城拦腰斩断。后来改为修高架桥跨过,但影响景观。再之后挖掘隧道钻过去,保护了自然风貌。尚珩说,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保护措施。
对于长城的管理和审批也在趋严。以前长城被列为古建筑,现在则归入古遗址。尚珩解释:“要注意古建筑和古遗址的保护理念完全不一样。不能把一个古遗址恢复成原来的建筑形制,比如圆明园,它是一个古遗址,但它也是建筑,如果按照古建筑去保护,那就要恢复到康熙和乾隆时的样子了。”
长城以前的保护理念是古建筑,所以我们看到了恢复成明朝形制的慕田峪、八达岭。“所有垮塌的都修好,垛口原来有多高就修多高,原来用什么砖就用什么砖,恢复成某一个时间点的形制,这是对古建筑的做法。如果是古遗址,就不把它原封不动地恢复起来,将塌未塌的支撑住,不再把塌的部分补回去。”
还有一个区别,古建筑在保护规划之前很少做考古发掘工作,长城被纳入遗址之后,对其进行保护之前,国家文物局的批复上列在第一位的总是“应组织专业机构开展考古调查、勘探和必要的考古发掘”。
“这说明我们对长城的认识由古建筑层面转变到了古遗址,那么我们会按照遗址的保护理念和方法,对长城进行保护,最明显的就是抢险加固,最小干预,这也更符合国际上对古遗址保护的主流。这次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做的几个项目都是按照古遗址策略来做,能不动就不动。比如修箭扣长城就把上面的一些树都保留了,在以前是绝对不会留下来的。”
尚珩说,实际上按照古遗址的理念策划,会给施工和管理增加很多麻烦,因为需要评估,树是否碍事,是否会威胁长城安全,但是保留的效果更好,公众可以看到更自然的长城风貌。
为了在长城的保护上少出现或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,尚珩和小站的志愿者以及许许多多人还将继续努力下去。文/本报记者 王勉 供图/尚珩
关键词: 长城